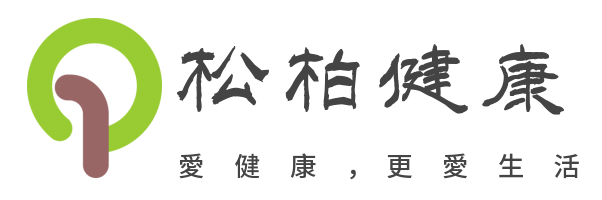「就想趕緊把手術做了,過上正常人的生活,就像他們一樣,淹沒在茫茫人海裏,過着最普通的生活」,王梓淇指着一米開外的遊人對我說。
我和王梓淇坐在坪山馬巒山公園的涼亭裏,這是周日的下午,我倆身旁的石凳上,前前後後坐過好幾撥人,有帶着孩子的年輕母親,有三五成羣嘰嘰喳喳的少男少女,有熱熱鬧鬧的一家三代。
她沒有避諱來來往往的行人,講起小時候村裏人的指指點點,讀書時男生們的嘲謔與肢體攻擊,「二刈子」、「娘娘腔」等外號……講這些的時候,她語調平靜。只有談起父母、哥哥對她的漠視與嫌惡,她語氣才激動起來,表情緊繃,神色裡帶着慍怒。
幾天前,王梓淇剛剛上過熱搜,關鍵詞是「雙性人」,鏡頭裡她樣貌清秀,長發梳成馬尾,看起來與普通女性並無差別。
從染色體來看,王梓淇的染色體爲46XX,與正常女性的染色體相同。不過,她既有乳房、子宮、卵巢、陰道等女性生殖器官,還有發育不完整的男性生殖器官——體外有指頭肚大小的陰莖,體內有睾丸。
王梓淇被診斷爲真兩性畸形,屬於性別發育異常(disorders/differencesofsexdevelopment,簡稱DSD)的一種。這是先天性疾病,據不完全統計,全世界DSD的患病率爲1/1500。
跟我見面之前,王梓淇去鹽田中英街幫人帶了點貨。做「水客」,是她的謀生方式之一。爲了這個活兒,她早上6點起牀,騎電動車,坐地鐵,換公交,光路上的時間就花了將近4個小時,奔波一個上午,刨去路費,賺了130塊錢。
馬巒山距離王梓淇的住處不遠,山不算高,爬上去只要一個半小時。這天她沒敢爬山,我們在公園涼亭坐了兩個多小時。近兩三年來,過度勞累、劇烈運動之後,她的腹部會劇烈地疼痛,這一症狀越來越嚴重,那種痛「難以形容,大概跟男性下體被踹後的痛感差不多」。
她擔心這是體內的睾丸在作怪。今年四月份檢查身體時,醫生建議她儘快手術,摘掉體內的睾丸。「隱睾將來有可能癌變」,醫生告誡她。
手術費讓王梓淇頭痛。摘掉體內的睾丸,再把外部的男性器官摘除,通過手術變成真正的女性,手術費大概要20多萬。
近10年來,王梓淇在深圳以打零工爲生,服務員、保安、水客、家政、快遞分揀員、外賣員……各種各樣的活兒她都幹過,銀行卡裏存款最多的時候,有4萬多塊。去醫院檢查身體每次要兩三千,每月服用雌性激素類藥物要1000多塊錢,這是她日常生活之外的必要開銷。疫情以來,她能找到的零工機會日漸稀少,多數時候靠喫老本生活。最窘迫的時候,她一天只喫一個饅頭,靠着老鄉、朋友一二百塊的接濟生活。
今年的零工市場不景氣,她一個月收入大約有2000多元,只能勉強支撐生活。以她現在的身體狀態和收入能力,靠自己攢夠手術費希望渺茫。

艱難漫長的路程:成爲女孩
王梓淇租住在坪山的一個城中村裏,房間沒有柜子,家具電器小而矮,1米高的冰箱,矮桌、矮凳、矮牀,抬眼看過去,屋子裡空空蕩蕩。她獨自居住在此,有時候房間裡太安靜了,她就跟Siri、小愛同學說說話。
她從臥室拿出一本發黃的舊書《男女生殖系畸形》,翻到186頁,那一頁是真兩性畸形的圖例。今年年初,她在深圳圖書館看到了這本書,書已經絕版,「全深圳的圖書館中只保存了那一本,還不外借」。她拍下了書的封面,在網上買了本舊書,從頭到尾讀了一遍。
王梓淇記不清楚,「身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」這個疑惑,從何時開始困擾她,可能是「從身體開始發育那會兒」,還有可能更早。
父母從小把她當男孩養,她在心裡一直當自己是女孩,小時候也總扎在女孩堆裏玩。初一她來了月經,「嚇得要死」,回家找母親,母親一樣慌了,後來還是鄰居姐姐給了她一片衛生巾。
她不喜歡太原老家的生活,親友鄰居當中,能讓她感受到善意的,除了借她衛生巾的姐姐,還有一個堂嫂。在學校裏,不少女同學保護過她。初中時同班一個女生,總會站出來幫她解圍,「男生給我起外號,從背後踹我一腳的時候,她都站出來維護我,跟他們吵架」。
「除了這些,我記憶裏沒有其他溫暖的東西。」
讀高二時,王梓淇被確診爲重度抑鬱,當時她已有輕生的念頭。她伸出手臂,給我看手腕上的幾個橢圓形疤痕,「那會兒拿刀削的,流了很多血我都不覺得疼,還在那裡傻呵呵的笑,我爸媽以爲我得了精神病」。
因爲抑鬱症,王梓淇從高中退學,去了家附近的飯館打工。攢了一兩年的工資後,她獨自去太原的三甲醫院做檢查,確診了自己的病。看到檢查結論上,自己的染色體與其他女性一樣,她慶幸不已。
拿着檢查報告,她從老家來到深圳。來深圳的前兩年,她先後在比亞迪和富士康做過工人。那時她還沒有服用激素類藥物,身上穿着女孩的衣服,面孔看起來「還是男孩子的臉」。
在一個工作環境裡待久了,周圍的風言風語壓得她喘不過氣,「吐沫星子能把你淹死」。同宿舍的工人也容不下她,有時出門她忘記帶鑰匙,回屋時敲門,其他人在門裡「裝聾作啞」。
在比亞迪工作時,王梓淇認識了朋友M,M也是雙性人,病症屬於男假兩性畸形,有乳房,沒有子宮卵巢,有發育不全的男性器官。
M認爲自己是女性,但身份證上寫着男性,一進工廠就被分到了男宿舍。王梓淇當時的身份證上,性別一欄也是「男」。進廠前,她花200多塊錢買了張女性的身份證,順利分配到了女宿舍。10多年前,在汽車站、網吧等地方,買張身份證不難。
除了M,王梓淇在廠裏沒有別的朋友。她和M總是結伴同行,周圍工友關於兩人身份的猜測和議論不絕於耳。幹了一年半,王梓淇受不了流言飛語,辭職離開比亞迪。
其後王梓淇去了富士康,工作一年後被辭退,沒有人告訴她辭退理由,她猜測還是因爲這個病。
M在工廠裏的日子,還要比王梓淇艱難許多。爲了掩飾身體上的問題,M每天要拿布條在胸部纏上十幾層,M也適應不了男宿舍的集體生活,「看着一屋子光膀子男人就難受」。
工廠生活再不如意,也比老家強。來深圳前,父母不許她留長髮,也不許她穿女裝。她身上的衣服,大多是哥哥穿剩下的。在深圳領到第一筆工資後,她開心極了,「想怎麼穿就怎麼穿,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。總算自由了,解脫了。」
離開富士康後,王梓淇沒再做過固定工作,她害怕熟人環境裡的歧視和孤立。這些年她靠各種零工謀生,工期最長的也就3個月。疫情前打零工的機會很多,有時她一個月能賺到五六千塊,能賺錢的活兒都辛苦,一天要忙10小時以上,不過她覺得充實,起碼沒時間「想東想西」,「倒頭就睡,起來就幹」。「倒頭就睡」對王梓淇來說,也是一種奢侈,患上抑鬱症後,失眠問題一直糾纏着她。
這些年王梓淇只回過老家一次,是爲了改身份證。更改身份證的過程很麻煩,她要先到醫院做各種檢查,由醫生出具性別鑑定書。再帶着這份鑑定書,找村委、街道、派出所依次蓋章,把身份證上的性別改爲「女」。
這次換身份證,王梓淇把名字也給改了。她原來的名字聽起來像男孩。「梓淇」,是她專門找大師起的名字,對方說她命裏缺水缺木,幫她取了梓淇兩字。她把姓改成了「王」,這是母親的姓,她覺得比原來的姓好聽。
拿到新身份證那天,她「抱着身份證一天一夜沒睡着」,躺在牀上,心裡像浪潮在奔湧,「好像人生有了一個新的開始」。
幾年前,王梓淇和M在網上結識了一些同爲雙性人的朋友,倆人被拉進一個30多人的QQ羣,羣裏都是渴望成爲女性的兩性畸形患者。目前這個羣的人數,已經增加到80多人。
羣友中,一部分人已做完手術,生活步入正軌。有的人以男性身份念完大學步入職場,攢足手術費後再選擇做女性。王梓淇心裡覺得遺憾,「其實我不該退學的,應該像她們一樣,先把書念好。」
有些羣友手術成功後步入婚姻,卻難於被丈夫的家庭接納。有些人原本是男假兩性畸形患者,藉助手術植入的人工陰道無法分泌巴氏腺液,婚後的夫妻生活要依賴潤滑液,「也是非常痛苦」。
相比其他類型的兩性畸形患者,在成爲女性這件事上,王梓淇更有優勢,她擁有完整的女性生殖系統,雌激素水平在正常女性的參考範圍內,睾酮值也遠低於正常男性。
王梓淇眼下的問題,卡在手術費用上。前段時間,她將自己的情況爆料給國內多家媒體,只有澎湃新聞回應了她。好在澎湃的報道吸引了公衆的注意,也給她帶來了更多的曝光機會。
「做這個決定前,是不是鼓了很久的勇氣」,我問她。
她點點頭,接着說,「我有點破罐子破摔了,只要能做手術,其他都是次要的」。
無家的「女兒」
經過媒體報道後,王梓淇先後在微博、抖音平臺上了熱搜榜。半個月過去,她在輕鬆籌上的籌款數目,大約有3萬塊。
「這個離20萬還差好遠」,說這話時,我們正從公園返回她的住處,她臉上掛着疲態,不知道是因爲累了,還是心情的緣故。
在我們的接觸中,我能隱約感覺到,王梓淇迫切地渴望着一個結果。
我們第一次見面,約在她的出租屋裡。期間街道辦工作人員來訪,請她填寫救助款的申請表。她的現狀經媒體報道後,街道辦爲她申請了一筆臨時救助款,數目大約幾千元,在填表的間隙裏,她幾次問起對方「這個能申請下來嗎,什麼時候有結果」。
王梓淇老家位於太原市郊,父母常年做小生意,日子還算寬裕。這些年,她主動跟父母溝通過很多次,一年一年下來,結果令她沮喪、失望再到絕望。
迴避和推卸是父母一貫的態度,「他們說,你沒有病,你男孩子做得好好的,非要做女孩幹什麼」。再爭吵下去,父母的話更難聽,「因爲你我們都抬不起頭,臉都丟盡了,被別人戳了多少脊梁骨」。
在王梓淇的講述裏,她在家裡處於被孤立被邊緣的位置,父母與哥哥「都覺得我給這個家丟人了」,「他們三個是一夥,我是一個人」。
肢體和語言暴力充斥在她的成長記憶裏,父母、哥哥打起她來下手都狠,「拿棍子打,帶着怨氣打,覺得我是家裡的恥辱」。她扯開上衣領子,給我看左胸口一個三角形的疤痕,「十幾歲的時候,被我哥拿刀捅的,送到鄉下醫院流了一晚上的血。就因爲我跟父母頂嘴,他要維護他們。」
「我哥哥牙磕掉了,他們能花三萬給他補牙,都不願意花一分錢給我治病。」她苦笑着跟我抱怨。
父母的偏心和冷漠令她憤怒,「他們總說我給他們丟人,他們就沒想過,把我生成這樣,我有多痛苦。要是小時候他們給我看病,做手術,我也不可能過成現在這樣」。冷靜下來,她又覺得父母不容易,「在老家,別人罵他們的話也很難聽,『上輩子造了什麼孽,生了個什麼』」。
她跟我提起家裡的徵地補償款,屬於她的賠償大約有8萬,這是老家的工作人員通知她的。全家的賠償款,統一打到了父親的賬戶上。
在與父母的關係,以及這筆補償款的問題上,王梓淇背負着社會環境的壓力,她也有輿論上的顧慮,因此顯得猶移而矛盾。
我們第一次碰面時,她告訴我,她不打算問父母要這筆補償款,「他們也要養老的,我不想讓別人說我不孝」。
第二天我們再見面時,她跟我說起的頭一件事,便是前一夜與母親的爭吵——她撥通了母親的電話,母親說的第一句話是「你在深圳10年賺了多少錢」,兩三句對話過後,倆人又是一番爭吵,母親又一次拉黑了她的微信。「我爸媽眼裡就只有錢」,她衝我抱怨。
「打電話給媽媽,是不是想拿回補償款」,我問她。
「只是想跟他們建立聯繫」,她說。
兩天後,王梓淇在微信裏告訴我,她打算通過法律手段要回這筆錢。
在那個由兩性畸形患者組建的QQ羣裏交流時,王梓淇發現,大多數羣友與她境遇相似,「能得到家庭的理解支持的人很少」。即便做完手術成爲女性,生活步入正軌,她們依然無法緩和與父母的關係,「這個沒法調和,除非父母很開明」。
有一年,羣裏十幾個朋友在北京搞了個聚會,王梓淇也去了。聚會是北京的羣友Q發起的。羣友當中,Q的經歷最勵志。Q十幾歲被父母趕出家門,獨自謀生。Q很能喫苦,爲了賺錢「什麼都活都願意幹,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」,一番打拼後Q有了自己的生意,賺了不少錢,她做了手術,還在北京買了房和車。
得益於事業上的成功,Q與原生家庭恢復了來往。「她開着100多萬的路虎回了老家,衣錦還鄉啊,全村的人都圍過來看。以前不來往的那些親戚,也都上門了。」王梓淇轉述起Q的這段經歷,一臉揚眉吐氣的痛快勁頭。
「怎麼反駁?」
通過媒體求助這個事上,王梓淇的閨蜜何冬冬一開始是不贊成的。何冬冬擔心網絡上的惡意攻擊,會給王梓淇帶來二次傷害。但她能理解王梓淇的無奈,「籌錢這個事情,不是她不夠努力,她已經很努力了,見不到任何效果,籌不出那麼多錢。」
大多數時候,談起那些被歧視,被孤立的處境時,王梓淇語氣平和,幾乎沒用過抱怨的詞彙,平靜得像是在描述別人的經歷。
只是,傷害很難被輕描淡寫地抹平,「別人說難聽話,咽不下這口氣,自己跟自己生悶氣,就在心裡憋着。會失眠,整夜睡不着。」
何冬冬跟王梓淇合租過一年,王梓淇情緒失控的情形,她只見過一次。她跟着王梓淇做過一次兼職,「一起做事情的人裡面,有個女的說了句『不男不女』,雖然沒有指名道姓,一聽就知道是說她(王梓淇)的」,何冬冬心裡惱火,轉頭看王梓淇「好像沒聽到這話一樣」。
沒忍住火氣,何冬冬跟對方吵了一架。忙完回到出租屋,何冬冬看出了王梓淇的低落,「我問她,她說她很難過,她說你沒必要跟這些人吵,她對這些話已經習以爲常了。」
何冬冬勸她,「不能忍,該反駁就要反駁」。
「我怎麼反駁,你告訴我怎麼反駁。我就是這個情況,我怎麼反駁。」王梓淇反問道。王梓淇說這句話時的神情,還刻在何冬冬腦子裡,「感覺就要哭出來了」。
——「會覺得命運很不公平嗎?」我問王梓淇。
——「對」。
——「什麼時候最仇恨命運?」
——「最低谷期的時候,疫情那幾年,高中想自殺那會兒,就覺得命運對我不公,也抱怨過,爲什麼會這樣,是因爲我上輩子做了啥缺德事嗎,這輩子是不是來還債的。」
另一種生活
對王梓淇來說,何冬冬不止是閨蜜,也是她唯一的親人。倆人前年通過朋友認識,當時何冬冬剛來深圳,需要找住處,王梓淇提議兩人一起合租。
與何冬冬共同生活的一年多裏,王梓淇初次嘗到了家的溫度,「她(何冬冬)廚藝好,負責做飯,我打下手,我都有點飯來張口的感覺」。她感覺生活步入了正軌,「家裡有人牽掛着你,幹什麼都有動力,很有盼頭」。這一年,王梓淇停掉了抗抑鬱藥物,失眠的毛病也好了。
兩人合租半年之後,王梓淇向何冬冬袒露了身體上的問題。她當時的神態何冬冬記得清楚,「看起來很忐忑,感覺是鼓了很大的勇氣才說出口的」。
「怎麼會有這種病呢?」何冬冬心裡震驚極了,偷偷地在手機上查資料。很快,她便接受了王梓淇的情況,「你是成年人,了解了,自然就能坦然接受,把她當成一個普通人對待就好」。
去年,何冬冬回到貴州老家生活。又回到一個人的狀態,王梓淇很不習慣,「有家了,家人又離開了,適應不了這種感覺」。王梓淇又開始失眠,有時兩人的微信語音徹夜開着,她睡不着,聽着電話那頭何冬冬的呼嚕聲,心裡也踏實。
過去兩年的春節,王梓淇都是在何冬冬的家裡過的。何冬冬是家裡的獨生女,父母、奶奶都很疼愛她。王梓淇喜歡何冬冬的家庭氛圍,尤其是喫年夜飯的時候,「一家人圍在一塊,熱熱鬧鬧的,特別有感覺」。貴州菜口味重,王梓淇不能喫辣,何家媽媽照顧她的口味,所有菜都不放辣椒。何媽媽做菜特別好喫,她最喜歡那道梅乾菜炒肉。何媽媽認她做了乾女兒,去年春節給她包了個1000元的紅包。
看着何家其樂融融的生活,王梓淇忍不住在心裡做對比。「閨蜜爸媽也是做小生意的,也沒有什麼文化,爲什麼人家那麼通情達理,爲啥我父母就不可理喻」。
踏實溫熱的年味兒,在王梓淇這裡,又是短暫而倉促的。不管何家人如何挽留,王梓淇待上五六天便會離開。何冬冬能察覺到王梓淇的微妙心態,「自己有家回不去,又怕給別人家添太多麻煩。」
王梓淇聊起手術後的打算,「離開深圳,可能再換個名字,開始新的生活」。她那些做過手術的朋友們,幾乎都改了新名字。她沒想過結婚,「可能是我爸我哥對我都不好,我對男性有點害怕,很難信任」,之前那次北京聚會,發起人Q的選擇也讓她難忘,Q沒有要孩子的打算,「她說小時候把一輩子的苦都喫了,後面的人生只想爲自己活」。
將來,王梓淇想搬到雲貴或成都生活。去貴州,她有何家人的陪伴。不過她最喜歡成都,她去過一次成都,很嚮往那裡的自由和包容,「兩個女孩子在街上接吻,旁邊的人見怪不怪」。
王梓淇還想過,手術成功後她要自考一個學歷。她想做平面設計類工作,在深圳圖書館附近廣場上,她見過給人畫素描的街頭畫家,她喜歡那樣的工作狀態。
有空的時候,王梓淇會搭乘14號線地鐵,花上一個多小時,從坪山坐到市中心,再到深圳圖書館裡看看書,聽聽講座,或者在書城廣場上逛逛。
深圳圖書館這片區域,是王梓淇最喜歡的地方。這裡圖書館、書城、音樂廳、藝術館相鄰而立,一棵棵挺拔蔥蘢的小葉欖仁樹,在廣場上空織出一張嫩綠色的網。樹蔭下散落着各式的街頭藝術家,北邊樂隊的粵語歌唱得燃情快意,南邊的小提琴演奏像溪水細淌,廣場一角的畫家和手工達人們不怎麼說話,專注着手裡的事情。在這個以加班和快節奏著稱的城市裡,此處像是生活的彼岸。
「看看人家畫畫,聽聽樂隊唱歌,心情一下子就好起來了」,遊蕩在廣場上,她獨自享受着這份隱祕的快樂,陽光穿過頭頂的枝葉,灑在她的身上。
備註:文中人物何冬冬均爲化名。
文丨黃小邪
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
轉載需授權,歡迎轉發至朋友圈